作者简介:刘闯(复旦大学哲学学院、中国科学院哲学研究所)
【摘要】伦理学研究的道德价值与行为规范似乎无法在客观世界的经验事实中找到踪影,也不可能从其中推演出来。既然科学是研究客观经验事实的学问,那么伦理学与科学似乎无法相容。可是,人类是自然之物,关于人的客观事实似乎不可能跳出科学的范畴,因此,伦理学与科学的不相容是个大问题。然而,科学解释有两种类型:一种为研究事物“动力因”的进路,另一种为研究事物“目的因”的进路。物质科学的自然规范性属于前一种,达尔文进(演)化论则属于后一种。道德规范在前一种进路中得不到解释其实不足为奇,因为解释它需要知道它是如何演化出来的。达尔文早已有关于道德起源的思想和初步理论,之后演化博弈论又提供了更丰富的资源,但仍然与我们的目标存在差距。结合集体或社会实在论的相关思想,可以更有效地解决伦理学与科学相悖的难题。
【关键词】道德起源 群体选择 道德表达主义 集体意向性 社会本体论
一、“是”与“应该”的差距
伦理学是一门研究人类道德价值和行为规范的学问。历来的主流学派有功利主义(utilitarianism)和义务论(deontology),新近复兴的还有美德伦理(virtue ethics)。建立伦理理论或某些主义是为了给人类的日常道德行为提供普遍与抽象的描述和解释,找到解释行为所依据的道德价值和规范。(参见程炼)科学理论,如神经科学、心理学、社会学、人类学等相关理论,也是为了描述和解释人类的日常道德行为,这些行为中充满了道德判断与争执。人们一定会问,被科学完备地解释了的行为,还需要伦理学再解释一遍吗?如果说哲学解释比科学解释更抽象或普遍,似乎也说不通,科学发现的自然规律不都是普遍、抽象的吗?而如果说伦理学所解释的是科学无法解释的,那么人类的道德行为和道德规范是超科学、超事实的行为和规范吗?要注意的是,反问科学是否有可能完备地解释人类所有行为(其中包括道德行为),是无济于事的。因为即便科学仅有希望近似完备地解释它们,剩余的边边角角也绝不可能是伦理学各学派所关心的。
这样来看,“伦理学与科学的关系”和“心灵哲学与科学的关系”不无相似之处。即便科学解释了大脑的所有结构与功能,它仍然没有“触碰到”意识(consciousness)现象。这样的观点,就是在物质主义和科学主义盛行的今天,仍然是值得人们认真对待的。(参见Chalmers; Lavine)意识理论和伦理学这样的哲学领域,是科学无法触及的思辨哲学的“最后疆域”吗?
另外,姑且同意科学能够完备地描述、解释和预测所有客观事实,可能“超越”科学的领域也并不少见。数学就是一个例子,逻辑学亦不可能被囊括于科学之中。那么,意识现象和伦理现象呢?它们也像逻辑学和数学那样不从属于科学吗?逻辑学与数学之不属于科学,最重要的因素之一是它们独有的“规范性”(normativity)。比如,事实上现实中没有任何三角形的内角和精确地为180度,虽然现实中许多三角形近似于这个规范;事实上也没有任何人在思考推理时不曾违反逻辑规律,虽然现实中有人接近这个规范。规范性是一种在现实中有违反可能的必然性。地球上没有违反引力定律的运动物体,但是三个内角加起来不为180度的三角形到处都是,就是这个道理。道德规范似乎也有这个特性,它似乎也是一种现实中常有违反实例的规范性。而心灵哲学中的意识现象似乎没有这一层规范性,意识现象似乎超出科学是由于它的主观性和现象性。
程炼在他的《伦理学导论》中用了一章的篇幅来解释所谓“来自科学主义的挑战”。在引用了罗素的《一个自由人的崇拜》中的一段话之后,他写道:“如果科学说出了世界的真相,即一切事物,人类的和非人类的,都是特定的原子排列,那么价值何在?义务何在?”(程炼,第 72页)确实,科学所触及的是自然系统的结构与功能,其中包括动机、信念、策略、行动等关乎道德评判的人类行为。且不说所有这些最后都能被还原到它们特定的原子排列(逻辑或认知命题不同于本体论命题),但正如休谟所指出的,就算你对某个你需要下道德判断的行为观察入微,你能发现的不过是上面提到的动机、信念、策略和行动,而这些都是可以由科学的方法得到某种因果解释的。(参见休谟)但是,在你所作的观察、所建构的解释中,你始终找不到道德事实——找不到比如“善”或“恶”、“应该”或“不应该”这样的规范性事实。休谟这是从认识论的视角,提出了对客观道德规范或事实的怀疑。而摩尔著名的“开放问题论证”则试图从语意或诠释的角度指明如“善”这样的道德属性是不可能归咎于任何非道德的客观属性的。(参见摩尔)摩尔指出,在人们运用语言的时候,若某等价关系属实,可以由该关系直接推出答案的问题称为“关闭问题”。比如,既然“1+1=2”,那么“1+1<1000吗” 这样的问题就是关闭问题。但“善”的道德概念则不同,即便我们找到了与善等价的自然、客观属性——“幸福”,“幸福就是善的吗”仍然是一个开放的问题,可以有不同的甚至是相悖的答案。
然而,如果基督教的上帝存在,上帝的旨意定义了何为善恶,上帝的“十诫”给出行为规范,那么以上的问题似乎都不存在了。如果能够证明上帝的存在,伦理学与科学的不相容还成问题吗?同理,如果人的心灵是非物质的实体(即身心二元论为真),而科学只能研究大脑的结构与功能,那么,心灵哲学与科学的相悖还成问题吗?因此,尼采的“上帝之死”不但给现代人带来了许多道德上的困惑,也给现代伦理学出了难题。总结以上的讨论我们可以提出以下问题或问题域。本质为物的人体内(生理的和心理的)和之间(社会的)怎么可能存在伦理价值和规范?世界上可观测的、科学能解释的客观事实中似乎不可能找到道德事实,那么道德事实存于何处?道德事实不可能是宗教性的(上帝已死),也不可能是主观意志(皇帝或独裁者的意志不是道德价值或规范),道德不同于法律制度似乎也说明它不同于社会契约。那么,道德是什么?它从何处来?它在哪里?
二、达尔文论道德起源
之所以得出“不过都是特定的原子排列”这样的结论,罗素心中的科学观或宇宙观是有特定方法论的。西方文明在很长一段时期内,经验知识的楷模是天文学和物理学。而在这样的科学领域中,解释自然现象的核心方法就是测量物体位置和运动的瞬时状态,然后发现状态随时间变化的自然规律,这其中包括发现影响物体状态变化的外因。这一套描述、解释和预测自然现象的科学方法,之后被推广到化学、生物学、心理学等学科,以至于在科学哲学领域产生了“科学统一说”的理论。按照普特南(和奥本海默)的观点,统一的科学是最符合人们对科学理论之间关系的实际观察的假说。(参见Putnam and Oppenheimer, pp.3-36)而他们所说的统一科学乃是一种自上而下的还原性大统一。比如,从原则上讲,心理学的自然规律和基本事实可由生物学的自然规律和基本事实定义和推导,而生物学的同样可由化学的规律和事实定义和推导;如此类推,一直到最底部的原子或者基本粒子物理学的规律和事实为止。笔者在此无意为这样一种科学哲学理论辩护,想要说明的是,在描述、解释和预测自然现象的科学方法中,物理学的方法可以从原则上变成统一的或者普遍的科学方法,即所有需要解释的现象都必须被纳入其中。若真理如斯,确实很难想象在科学的规律和事实中找到道德价值和行为规范的影子。
可是,物理学的方法及其延展并不是科学研究的唯一方法。在科学方法论中,至少还有另一种描述和解释自然现象的进路。达尔文进(演)化论是在现代科学中标志这种进路的理论,但作为方法论,在达尔文之前就存在着演化或进化的思想,而达尔文演化论在现代生物学中也已经经受了多种修改。演化论概括地说就是:由于繁殖与自然资源的不匹配,自然界中的复制体(同类繁衍)通过自身的变化,在生存竞争中不断演化达到稳定状态(比如所属种群的生存或灭绝)的过程。(参见Mayr)个体的状态不再是由前一时刻自身和环境的状态来决定和解释,而是由自身所具有或将会具有的功能以及功能与竞争环境的适应度来决定和解释的。演化的方法并不仅适用于生物体。虽然自然界中鲜有非生物的复制子,但无生命的人造复制子多种多样——它们的变化完全可以是演化过程。许多演化生物学中的思想实验,就是靠计算机营造的复制子来做“实验”的。如果可以称以物理学为典范的进路为“动力因”进路,那么演化论的进路可以叫作“目的因”进路。熟悉亚里士多德“四因”说的读者应该很容易理解这样的称谓,虽然我们并不是在沿用亚里士多德的哲学理论。(参见Taylor)
按照西方的传统,在达尔文演化论之前,道德价值和规范仅仅属于人类,其他动物是没有道德可言的,而这种绝对的分割线是造物者的意图。哲学家谈论道德、研究伦理时是不关心,也不可能关心道德的自然起源问题的。造物者给予了人类识别善恶和对错的能力,因此就有了伦理学——就这么简单。达尔文在发表了《物种起源》之后,一直对人类道德的起源问题保持沉默,原因是可想而知的。如果人类从低等动物演化而来,那么除非相信从猿到人的过程中造物者插了手,在适当的时候把道德能力给予了演化成功的人类,否则就无法对伦理学的来源作出与传统宗教相容的说明。人类识别善恶、对错等的道德能力必然是本来就有的吗?猿人、类人猿以及更加低级的动物种群也有道德价值和规范吗?什么样的自然条件足以产生伦理属性呢?达尔文在沉默了12年之后发表了他的《人类的由来及性选择》一书。(参见达尔文)当然,《物种起源》是在达尔文形成了他的进化论思想之后多年,因危及首发权的顾虑才撰写发表的,所以,达尔文对该问题的沉默其实延续了更长时间。对这个问题的担忧也是他迟迟不愿发表《物种起源》的原因之一。因此,达尔文在《人类的由来及性选择》一书中关于人类道德起源的言论,无疑代表了他十分成熟的思想。
在罗列了大量证据说明人类是由动物演化而来的之后,达尔文分别在第三章和第五章论证了人类道德起源于动物的低级(准)道德行为的思想。人类是社会性动物,具有社会本能(social instincts);而这种本能中已经包含诸如同情心、互助意愿、求荣誉避耻辱之心等道德感。这些利他本能[1]至少普遍存在于大型哺乳动物种群中。不仅在野生种群中可以观察到,在被人类驯化了的如马、狗、牛等种群中,利他本能的表现尤为突出。如果可以把动物的道德品质和行为列出不同的等级,那么在达尔文看来,非人类动物无疑具有这些品质的低级形式;而且虽然低级,但可以十分优秀。狗的忠诚、马的勇敢、牛的善良,在达尔文看来不比人类具有的这些品质低劣。但本能终究是本能,并非自主自愿的行为。至于动物利他本能的起源,达尔文推测有两个源头:一是亲情的延伸,二是群体间的选择竞争(group selection)。动物对亲属的利他情感与生俱有,可以从繁殖中基因的保存来解释(并非达尔文的解释,亦可有其他解释)。[2]粗略地说,群体选择的概念就是,群体之间的竞争可以使得群内个体互助的种群在自然选择中胜过群内个体缺乏互助情感的种群,因此,具有利他本能的个体借助于群体自然选择的机制得以延续和传播。[3]那么这种本能是如何演化成人类具有的道德品质,如何会出现道德规范的呢?达尔文从三个方面回答了这个问题:智力发展、语言和习俗的作用。达尔文生活在英国维多利亚时代,后果功利主义是那个社会的道德思潮。在从动物的低级利他本能到人类的道德感(moral sense)或良心(conscience)的演化中,个体首先需要具备长期记忆和筹划未来的能力。记忆让个体在行动之前或前瞻之时有审慎(deliberation)的可能;当然,审慎也是智力发展的结果。有了这种能力,后果功利主义的伦理观就不显得那么遥远了。在达尔文看来,语言对道德观在动物社会中的成熟,主要起着成员之间相互督促的作用;群体中发展出的一套言语系统,成为个体之间用它来褒贬对方的意念和行为的工具。久而久之,这种相互褒贬便会在成员心中产生良心这样的道德情操。
那么,由利他本能、智力、语言和习俗的发展而导致的道德感,必然会产生如后果功利主义的伦理观,或者为某种道德规范奠定基础吗?达尔文的回答是否定的。但无论我们是否接受达尔文这样回答的理由,达尔文道德起源说的哲学意义是无可非议的。
达尔文认为,人类从动物演化而来的道德感不构成产生道德价值与行为规范的充分条件。如果人类在蜜蜂的条件下演化而来,谁能说我们的未婚女子不会把屠杀她们的兄弟作为她们的“神圣职责”呢?(参见达尔文,第73页)那么,达尔文的意思是说自然演化出来的道德观念必然是相对主义的吗?比如可以问,北美印第安人的道德观与北欧白种人的道德观不但不相同,而且应该就是不相同的道德系统吗?当然,在达尔文时代道德相对论还没有被提上哲学家们的日程,但就如何解读达尔文的这个思想,笔者认为可以这样来看。无疑,达尔文认为,利他本能、智力、语言和习俗这些属于种群自身的性质,在足够不同的自然选择环境里,会演化出不同的道德感。依据现代人类学的成果,这一点似乎无可置疑。可是,这些自然演化出来的道德感最终都能够演化成种群的伦理观吗?现代伦理学关于道德相对论的争论,考虑的恰恰是在地球上不同环境中演化出来的原始道德感是否可以通约、是否有可能在理性原则下得到普遍意义上的修正和统一。换句话说,如果蜜蜂演化出了与人类同样的智力、语言和习俗,它们会看不到它们“社会结构”的不合理吗?似乎没有理由相信,蜜蜂种群现存行为中类似道德的行为,在智力和语言等条件具备了之后,仍然是自然选择的最优结果。
从另一个角度来看,伦理学中诸多派系理论的争执不下、各种反例的层出不穷,难道不正说明了道德价值和行为规范的相对主义观点是正确的,道德观不外乎不同种群在不同自然条件下演化博弈而产生的行为规范吗?
三、道德规范与演化博弈
达尔文对道德起源的原始思考,以及沿着整个以演化论为方法的科学解释进路,无法解决的问题还不只有上面提到的这个。道德感与道德价值和规范之间的差距,不仅仅可能导致道德相对主义,其他还有很多相关的问题。比如,人与人之间的公平感、正义感是从哪里来的?达尔文的起源说中用了亲情延伸和群体选择这两个演化机制来解释利他本能(相互协助、善待他人等良心)的起源,可是,无论亲情还是群体间的竞争,都离不开公正或正义感,而上面提供的资源似乎无法解释这种原始道德感的起源。上文提到,达尔文的道德观是受到19世纪英国维多利亚时代后果功利主义伦理观深刻影响的。回推两三个世纪,到了16—17世纪的英国,霍布斯伦理学的基本思想则完全不同。在霍布斯那里,利他本能是不存在的,基于“个体的根本自私性和野蛮性”与社群共存条件下“分享有限资源的必要性”这两个相悖的自然条件,人类的道德感只可能是契约性或博弈性的理性原则。现代伦理学中的所谓“利己主义挑战”(参见程炼,第一章),即本能自私的演化生物群中道德感和道德观如何可能的问题,是达尔文无法回应的。可以看出,人性本善还是恶的问题转化成了人性本利他还是利己的问题。若是人性本善,社会公平正义从何而来?若是人性本恶,公平正义源于理性契约,人与人之间的善意又从哪里来?难道“善皆伪善”不成?
基于演化论来探讨道德起源和本质的现代进路,在笔者看来有两大类。一类多以深具哲学兴趣和修养的实验科学家为代表,另一类则以偏爱理论数学模型的哲学家为代表。前者为一个大类,其中包括了演化伦理学(evolutionary ethics)、道德心理学(moral psychology)和基因—文化协同演化论(gene-culture coevolution)等。(参见Boehm; Flanagan; Richardson and Boyd)演化伦理学直接继承了达尔文的经验观察和分析传统,而道德心理学注重研究在整个心灵的演化中道德情感是如何演化而成的。众多学者中特别值得关注的,是著名的比较心理学家托马赛洛(M.Tomasello)近年来极富创见且影响深远的工作。他从大猩猩和儿童的对比实验研究中,加上集体意向与承诺的哲学思想,为科学解释道德行为以及思维、语言等其他现象的演化作出了重要贡献。(参见Tomasello, 2014; 2016)相比之下,后一类的规模小一些,笔者认为代表性人物有斯凯姆斯(参见Skyrms, 2003; 2014)和亚历山大(参见Alexander);他们的工作扎根于现代演化博弈论,深入探讨了“合作”“信任”“公正”和“报应”等道德感的起源以及道德观的界定。国内这方面的研究才刚刚起步。(参见王巍,第109—115页)
演化博弈论(evolutionary game theory)是演化论和博弈论相结合的产物。梅纳.史密斯(J.Maynard.Smith)为其创始人之一,他的经典著作《演化与博弈论》为演化博弈论奠定了基础。(参见梅纳.史密斯)博弈论原本是关于理性个体依照功利博弈的原则、为寻求最大利益而选择其行动策略的学问。其基本逻辑结构,非常粗略地说,就是把人生看作一条不断选择最佳行动策略的道路。在每个选择点上,环境给出可能实现的条件及各自的概率,环境对博弈者呈现有限个互斥的行动策略。每个策略在相应的条件下有各自的“收益”(payoff)。对每个策略求各个可能环境条件的加重收益值之和。如何比较各个总收益、依据怎样的原则选择行动,这便是博弈论的内容。纯粹自顾[4]、绝对明智(冷血)是博弈论的假设之一。它首先在经济学中得到广泛应用。梅纳.史密斯意识到,博弈中的收益值不仅适用于明智个体的社群,博弈也不仅存于人间;大自然就是最大、最原始的博弈场!生存竞争、自然选择就是一个博弈过程。生物体个头的大小、麟角的粗细、獠牙的长短、奔跑速度的快慢等,都是自然的生存策略。可是,什么是生物体的“收益”?它如何用数值来度量?自然又如何“理性地”在不同的策略总收益中作出选择?梅纳.史密斯进一步认识到,生物个体的“适应度”(fitness)可以替换经济学中的“收益值”,而人类根据总收益对行为策略所作的选择,到了演化博弈论中,就成了自然选择:强者存,弱者灭。从种群的观点来看,比如,某种群中“选择了”大獠牙的变种比小獠牙的变种适应度高(即留下更多后代),那么自然选择就会随时间推移让大獠牙变种逐渐在种群中占据多数。“策略”“收益”“选择”等与人类理性有关的范畴,被经过“祛魅”还原到自然环境中,拓展了达尔文演化论的范围。其实,《人类的由来及性选择》一书中的“性选择”部分,从今天的观点来看,就是达尔文的演化博弈论理论;性选择就是一个两性之间博弈的自然选择过程。演化博弈论也叫依赖频率的演化论(frequency dependent evolution),而传统演化论可以说是其中的特例,即频率依赖性为零的演化博弈论。(参见诺瓦克)
之后,演化博弈论“重返”经济学、社会科学,将演化论的概念和方法运用于解决诸如“囚徒悖论”这样的经典问题(参见艾克斯罗德);另外,“文化演化论”(cultural evolution)也重获新生,使得前面已经提到的文化-基因协同演化论成为热门理论。依据诺瓦克(M.A.Nowak)的最新版演化动力学理论,演化博弈论不但统一了自然选择和理性选择、生物演化和文化演化、表征层面(phenotype)和基因层面(genotype)的演化关系,而且还统一了无限、无结构、连续的大型种群模型与有限、有结构、离散的小型种群的演化过程。(参见诺瓦克)在诺瓦克之前,复制子方程改进了梅纳—史密斯的经典理论,为无限、无结构的单性连续繁殖(复制)过程建立了动力学方程。经典理论是依靠如ESS(演化稳定策略)点这样的演化相空间中的特殊点的几何性质来刻画种群表征层演化的情况(即演化景观[evolutionary landscape])的。复制子方程的发现,使我们能够如在物理学中求解粒子的运动轨迹那样,求解出持有某种生存策略的生物体在演化相空间中的演化轨迹。但是,生物种群既不是无限的,也不是无结构、纯粹随机交配的,因此,为了模拟更多更真实的种群演化过程,诺瓦克的演化动力学从生物演化最基本的特征开始——复制、随机、突变、竞争、选择,采用体现这些特征的最简模型——莫兰(Moran)模型,对各种不同的有限种群结构(或结构元),运用图论(graph theory)和图博弈论(graph games)数学方法,打造出在笔者看来至今最有解释力的演化博弈论动力学。
斯凯姆斯的工作主要集中在探讨演化博弈论对合作、社会结构以及符号交流、语言的起源的解释作用。(参见Skyrms, 2003; 2014)合作的范畴当然牵涉到公平合作的概念。这些不仅仅是道德起源和本质的基础,也是诸如社会制度、政治体系、法律等的起源和本质的基础。从这个意义来说,上面提到的和尚未提到的,以演化论进路探讨道德起源和本质的方法,其实都具有这个特征,即它们似乎同样在为与道德/伦理相邻的领域提供起源的解释。制度、法律、政治,乃至礼仪、品味等,所有这些因为人类为群居动物,都可以在不同程度上是演化博弈的结果。那么问题是:是什么具体的演化博弈过程最终产生了道德而不是法律?或者说,是什么因素使得人类社会在法律、制度、礼仪等限制个人自由的社会机构之外还有道德?对于这个问题,亚历山大的工作试图给予直接的回答。
演化博弈模型在亚历山大看来分为两种:一种是复制子方程模型,另一种是各种社会网络(social network)上的博弈模型。(参见Alexander)但在今天看来,这样的区分实际上是没有必要的。(参见诺瓦克)但这并不影响亚历山大用这些模型探讨合作、信任、公平与报应在模型中演生的可能性。比如,对于“公平”(fairness),模型种群为一个仅存成对随机博弈的有限群体,模型博弈为“分蛋糕”。这个种群的复制子方程可在各种不同的分蛋糕策略中得出唯一的ESS解。不懂这一套数学工具的读者也不难猜到方程的解是什么。如果你和我分蛋糕,在其他条件均等、我俩背景条件对称的情况下,我得90%、你得10%肯定不是演化稳定策略解。无论我俩明智与否,甚至我俩是人还是猫也无关,复制子方程的ESS解都是50—50,平均分配——这就是“公平”的理论基础。然后,亚历山大把同样的问题放到书中选择探讨的各种图博弈模型中。这些模型意在反映种群中不同的“社会结构”对演化博弈结果的影响。书中选取了四大类这样的数学模型来讨论:格子模型(lattice models)、小世界模型(small-world models)、有限维度模型(bounded-degree models)、动力网络模型(dynamic networks models)。需要注意的是,每一个模型类都包括众多不同的模型。如果探讨其他问题,每个模型都可能给出不同的答案。可是,和复制子方程的答案一样,平均分配是所有这些模型给出的唯一答案。虽然答案是人们早已知道和相信的,但是得到这样的理论解释仍是一件了不起的事情。问题是,这还仅仅是答案的一部分,因为虽然平均分配是你我都能接受的分配,为什么说它是“公正”的分配呢?换句话说,以上的理论解释也许可以说明,为什么某社群的社会制度中有平均分配这样的社会习俗或契约,但是,为什么它会成为道德规范呢?[5]
这个问题与上一节最后的问题相同,都是在探问由演化博弈得到的种群道德感或社会集体行为如何成为道德价值和行为规范的基础。从种群/社群的个体心理与社会行为来看,“合作”可以是为了生存(社会需求)而产生的心理机制,与同情、利他无关,而后者是“善”的本质。“信任”与“真诚”之间也有同样的关系和差距。社会契约性信任离以诚相待还有很大距离,而后者是“真”的本质。“公平”也一样,上面已论及。而“报应”(retribution)是与良心相关的范畴。“报应”的社会心理机制可以是功利性的,它与“自觉”或“慎独”这样的良心概念也有差距。因此,本文第一节中提到的“是”与“应该”的距离似乎仍然没有完全消除,道德感的存在或公平分配制度的存在似乎得到了演化博弈的解释、成为客观事实,可是在它们之上还存在“道德事实”吗?
四、社会实在及其演化
上文提到道德“规范性”或规范事实与客观事实的差距,其中一个很棘手的问题是:科学似乎只能通过发现自然规律来解释和预测客观事实,凡是客观规律限定的,任何人或物不可能违反,可是道德规范完全不是这么回事。因此就有了“道德价值和规范要么不存在,要么是主观意志的产物”的哲学观点。本文第二节讨论了科学解释的两大进路,以动力因果为解释模式的科学确实对缩短伦理学与科学的差距没有帮助,所有的希望都寄托在达尔文范式或目的因果解释范式的科学解释上了。可是依照第三节最后的观察,差距似乎仍然没有完全消失,演化博弈论的各种模型似乎仍然达不到解释规范性道德价值和规范起源的目的。
从最基本的原则来说,自然界中演化博弈的过程是个体之间利益博弈的过程。所谓个体之间可以是人与人之间,也可以是细胞或基因之间、部落或民族之间。本文第二节中讨论的那些达尔文关于道德起源的观察,许多都是关于动物个体在面临利益冲突时利他本能如何最终得胜的案例。这就是演化博弈论的雏形(参见Brown),动物界道德价值和规范的起源原则上就是这样一个过程。假设在某种群中,个体之间仅仅存在原始的“道德情感”,但是没有任何规范性的道德范畴。比如,虽然我向你承诺过,但到时我觉得想帮你就帮你,不帮你我也没有责任。个体间靠着同情、互助等本能,依靠环境和内在动力,凭机会维持生存。然后,由于某种原因,种群中出现了一个或一小群持有道德规范概念的个体,它们主张公正对人对事的原则,主张对偏离该原则的个体施行严厉处罚,同时还制定出解决利己—利他利益冲突的各种策略。如果自然环境和与其他种群的竞争使得该个体或小群体得以在这个种群中繁衍扩充,以至于最终占领整个种群,那么这个种群中从此便有了道德价值和规范。否则,如果该道德特性最终遭灭绝,那么说明这个种群的自然状态在道德特征这个维度上是ESS状态,不可入侵。[6]
选择讨论这样一个过程,笔者并非故意张扬霍布斯、康德、罗尔斯传统的伦理理论,贬低休谟、斯密、密尔传统,而是要指出这样一个事实:动物界,特别是灵长类,同情、合作、抱团御敌的本能很可能“生而有之”,并不需要演化博弈论来解释其起源。比如,依照诺瓦克的演化动力学,细胞、器官等个体层次之下的“群体”都具有合作的本能,都有“利他”倾向。而个体之间的社会/利他本能,或许就是体内同类本能在个体层面涌现的反映。(参见诺瓦克)可是,人类个体在合作、互助的过程中产生的强烈的公平感、责任感、自由感(即相互尊重)等,却似乎是独特的社会本能。上文提到,达尔文在他的书中推测,如果人类换了昆虫的演化环境,我们的道德行为是否会跟它们的一样。笔者认为不可能,因为即使在奴隶社会,主奴关系也并非绝对服从,也具有公平对待的道德规范。某奴隶主长期违反规范,奴隶起来反抗常常会得到社会的支持,至少是道义上(即道德上)的支持。
不难看出,从纯理论设想的演化博弈例子中很难得出确定的答案,其中有很多原因。首先是无法确切选择互斥的博弈策略。需要表征的差异是,原始利他情感产生的合作,以及持公正原则的利他情感产生的合作。可是,持公正原则和不持公正原则怎么界定?纯属个体心理素质呢,还是某种道德理念?再有,即使能将两种策略精化到互斥的程度,它们之间博弈的收益如何刻画?稍事思考就能看出,这种收益是非常难确定的。笔者举出这个例子也是想说明下面这样一个用演化博弈论来解释道德起源的两难。一方面是复制子方程或演化动力学方程能够得到确定解的博弈,比如重复囚徒困境博弈、重复瓜分蛋糕博弈或者重复猎鹿博弈。(参见Skyrms, 2003)但正如上文对亚历山大著作的讨论所示,能得到的结论不足以回答道德价值和规范起源的问题。另一方面,直接模拟道德起源的博弈过程又无法套用现成的方程来求解;挑战有多方面,参数太多只是最明显的一个。
在现代著名的伦理学家中,艾伦·吉巴德(A.Gibbard)应该是很少的几位直接诉诸演化博弈论的概念来说事儿的哲学家之一。在他的《明智的选择,贴切的感受》一书中,吉巴德依据粗浅的演化博弈论概念(没有具体分析博弈例子)建构了一套自然主义规范理论,而道德规范即为该理论中最重要的规范。(参见Gibbard, 1990; Alexander)从上文的讨论不难看出,吉巴德的理论是达尔文理论的自然延伸,而他的特殊贡献是下面这样一套思想。从人群社会日常的交流和行为中可以观察到很多人们用道德规范(moral norm)来评判和协调自己和他人情感的例子,而道德情感(moral sentiment)是被道德规范驯服了的理性(rational)情感;并且这种接受社会规范管理的理性情感,就像达尔文早有预料的,是人类长期演化博弈过程的产物。用吉巴德的话来说:“何为接受规范?我用一套关于接受规范的假设性演化心理学来回应这个问题。所有物种都会面临经常出现的演化交易(bargaining)情景,其中需要博弈理论意义上的协调。像我们这样一个具有语言和复杂社会性的物种,应该会演化出运用语言来协调交易的机制,而这个机制的运作就很像是人类对规范的接受。这套机制的主要功能就是协调行动——部分通过协调信念和情感。接受规范就是在这样一种心理学中被解释的。”(Gibbard, 1992, pp.943-944)
达尔文的道德起源论仅仅说明了同情互助这样的社会性情感的演生[7],而吉巴德探讨的正好是本文最关心的问题——平等相待、服从规范等道德情感和价值的起源。吉巴德著作的另一个目标则是回应本文开头提到的摩尔的开放问题,即如何填平事实与规范、事实与价值之间的鸿沟。笔者认为吉巴德的理论代表了道德哲学中表达主义(expressivism)学派的卓越成就。按照吉巴德的说法,接受规范并不是接受一套事实陈述,而是接受一套如何相信事实、感知事实,如何依照规则行事的态度或方式。而这种态度就是理性态度的本质。做一个有道德的人,就是做一个明白自己和他人的欲望、情感、信念、策略的人,做一个在待人接物上体现自身道德准则的人,而不是一个相信道德原则、传扬道德说教、探究道德事实的人。当人们在日常生活中对自己或他人的信念、情感和行为作出道德评判时,他们的话所表达的不是命题式的道德陈述,而是表达了某种道德态度——道德情感和对道德规范的服从。
虽然作为哲学家手中的“可能性故事”(likely story)式建构,吉巴德的道德起源说可算高明,但明显的问题至少有两个。一个就是上文已经提到的问题:既然用到演化博弈论或者演化动力学的资源,就需要建模解方程。如何模拟社会交往合作中有规范心理和无规范心理在两种策略的博弈?两种策略如何做到互斥?博弈收益如何定义和度量?另外,即使能够建构出合适的量化模型,怎么得到实验验证,哪里去找经验证据呢?
总而言之,人类遵循原则理性地处理社会实践的策略在演化博弈过程中的胜出,仍不足以回答道德价值和规范是如何演化出来的。因为,道德从理念上说,并不仅仅是智力(intelligence)与理性(rationality)结合的产物。第三节中提到的托马赛洛的工作,加之近期哲学领域中关于社会本体论的学说,为强有力地回答这个问题提供了资源。(参见Tomasello, 2014; 2016)托马赛洛的目标比吉巴德更高,他通过比较黑猩猩和人类儿童的心理实验,试图找到人类思想与道德的起源与本质。而他学说的基础则是“集体”这个范畴。演化博弈在人类的进化过程中,最终得到的最基本的结果就是这个“集体性”。这是一个从“我”到“我们”的根本性转变。[8]虽然托马赛洛没有这样做,但不难想象设计一个博弈,博弈的策略一个以“我”为基本决策思想,另一个以“我们”为基本决策思想,最后得出后者必胜的结论。比如说,一个互助合作但没有集体概念和爱国之心的国家,在其他条件均等的情况下,一定比不过一个有集体概念和爱国之心的国家。托马赛洛的成果之中不但有道德价值和规范的确立,还有思想、文化、制度、历史乃至文明的出现。而底定(grounding)托马赛洛的这个体系基础的是集体意识和社会实在的哲学思想资源(参见Bratman; Darwall; Gilbert; Searle),这一点托马赛洛自己在多处提及。粗略地说,托马赛洛通过比较黑猩猩与人类儿童在各种不同合作实验环境中的表现得出结论说,儿童合作有一种集体责任感,会自然而然地要求自己和合作伙伴遵守合作规则,其中有些规则似乎是先天具有的,而有些规则是事先默认好了的。黑猩猩则没有这种集体责任感。回到达尔文的原始思想,他似乎仅仅注意到了灵长类动物与人类共有的在同情和互助等方面的社会本能,而托马赛洛通过对比实验发现,黑猩猩和人类在诸如集体意向性和集体责任感等方面都截然不同。而这种“集体责任感”正是公平正义感最基本的体现,同时也正好为上文讨论过的、用演化博弈论推演出来的理论结论提供经验支持。
当然,欲为达尔文辩护的人可以说,达尔文因受维多利亚时代道德观的影响和限制,着重列举了动物本能中“向善”的侧面。假如他更倾向于霍布斯或康德学派的道德观,他一定能够列举出同样多动物本能中“向公正”的侧面的。托马赛洛的实验观察结论,在笔者看来确实有一定的局限性。不难想象,他用来对比儿童合作行为的黑猩猩是实验基地圈养的动物。它们之所以缺乏集体责任感,很有可能是由远离自然栖息地的处境造成的。若能对自然栖息地的黑猩猩作同样的实验观察,很可能得到不同的结论。
回到第三节的最后的问题,本节的讨论消除了那里提到的差距了吗?道德事实存在吗?道德价值和规范是相对的吗?休谟的道德怀疑论得到回应了吗?摩尔的开放问题可以关闭了吗?本文一直关注的这些问题,无论是吉巴德的哲学学说还是托马赛洛的心理学实验,似乎都没能给出最终的解答。在笔者看来,实际上在托马赛洛援引的哲学资源中,社会本体论的进路就有缩小差距、回答这些问题的潜力。这方面的哲学文献中,塞尔的社会本体论学说最为引人注目(参见Searle),特别是他20世纪90年代提出的学说最近有了新版本,取名为“人类文明的逻辑结构”,说的是本体论上不过是特殊原子排列的人(罗素的说法)如何通过语言的“声明性”(declarative)功能,依靠契约精神造就社会实在的事情。人类文明社会的标志即为它的社会机构:政府、制度、法律、教育、经济、婚姻……这些社会现象虽然都有自然物作为载体,但它们是以社会实体而不是自然实体的形式存在于世的。没有它们背后的意向性,没有人们赋予那些自然物的意义,同样的“原子排列”既不会是政府,也不会是教育。
当然,所有这些社会实在都不属于道德范畴。前面说过,法律不是道德,礼仪不是道德,半自然半社会的原始家庭亦不是道德。那么道德在塞尔的体系中有地位吗?笔者认为,道德的实在性就是生活在上述社会实在中的人因受到各种社会机构的要求和约束,心中产生的、有外在依照(reference)的心理实在,或者说是一种道德心理实在(moral psychological reality)。这其中便存有道德事实,就是那些既是相对的、又是客观的道德价值和规范。休谟的怀疑论也可以由此得到回应。因为需要观察的不是人们自身的欲望和动机,也不是他们的行为,而是他们所在的社会实在对他们心理的影响和约束;这是一种从整体上观察人类群体才能看到的客观事实。而对于摩尔的开放性问题,我们可以说,道德属性确实无法从自然属性中推出,但客观属性并非都是自然属性,社会属性是人造物的特殊属性。不同于工商业产品,社会“产品”具有一种特殊的二阶属性。货币有形状、重量和质地等一阶自然属性,它们不能违反物理定律。但货币还有它成其为货币的二阶、非物质属性,而这种二阶属性遵循的(经济或社会)规律是可以被违背的。道德价值和规范也属于这一类二阶客观属性;与它们对应的一阶属性是人们的情感和欲望等心理属性, 也就是达尔文道德起源思想中的道德情感。
结语
虽然还无法严格证明,但本文大致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人和动物一样,从体内的生物博弈过程演生出同情、合作等向善的道德情感。缺乏正义感的原始向善情感,在合作(即演化博弈)中不为ESS状态,因而被具有正义感的个体成功入侵,以至于演化出含有正义感的向善个体的合作。随着智力的发展和语言的出现,各种保障正义向善的道德情感的种群或社会机构(比如政府和司法机构)得以演生;而它们的存在又巩固和促进了个体的正义向善心理机制, 最终形成道德价值和规范体系。也许这就是一个完整的关于道德起源的可能性故事。
【注释】
[1]本文用“利他本能”替代“社会本能”,以彰显达尔文用后者来指称非利己本能的意图。
[2]这里指的是“亲属选择”(kin-selection)的一套理论,达尔文的思想无疑是该理论的雏形。
[3]群体选择在现代生物演化论中是一个颇有争议的学说(参见Sober and Wilson),但在达尔文看来,那是理所当然的事情。不过,群体选择的问题是在基因学说出现之后才有可能提出的。
[4]本文用“自顾”(self-regarding)概念替代传统的“自私”(selfish)。
[5]如果读者不觉得应该在社会制度和道德规范之间作本质性区别,本文的最后会探讨这个问题。在那之前,笔者假设社会习俗、制度、政治、法律等范畴与道德伦理范畴有原则上的区别。
[6]这里用到的“出现”“繁衍扩充”“占领”既适用于生物演化,通过适当的理论拓展,亦适用于文明或文化演化现象。(参见Richardson and Boyd)比如,基督教成功入侵罗马帝国“种群”,或者儒家思想成功入侵汉朝“种群”,废黜了百家,都可以被纳入文化演化博弈论的例子之中,而且是属于复杂图博弈的例子。(参见Alexander)
[7]“演生”在本文中是“emergence”的意思。这个词通常译为“涌现”,笔者认为不够确切。“演生”是“演化生成”的意思,更为贴近“emergence”的原意。
[8]托马赛洛用到的是一组关联紧密的概念,英文词汇有:group or collective intentionality, joint commitment, group or collective beliefs, group or collective agency, 等等。篇幅有限,本文无法展开讨论这些概念和它们之间的关系。
【参考文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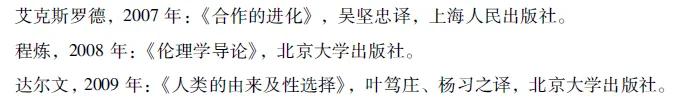

原载:《哲学动态》2024年第3期
文章来源:“哲学动态杂志”微信公众号2024-4-19


